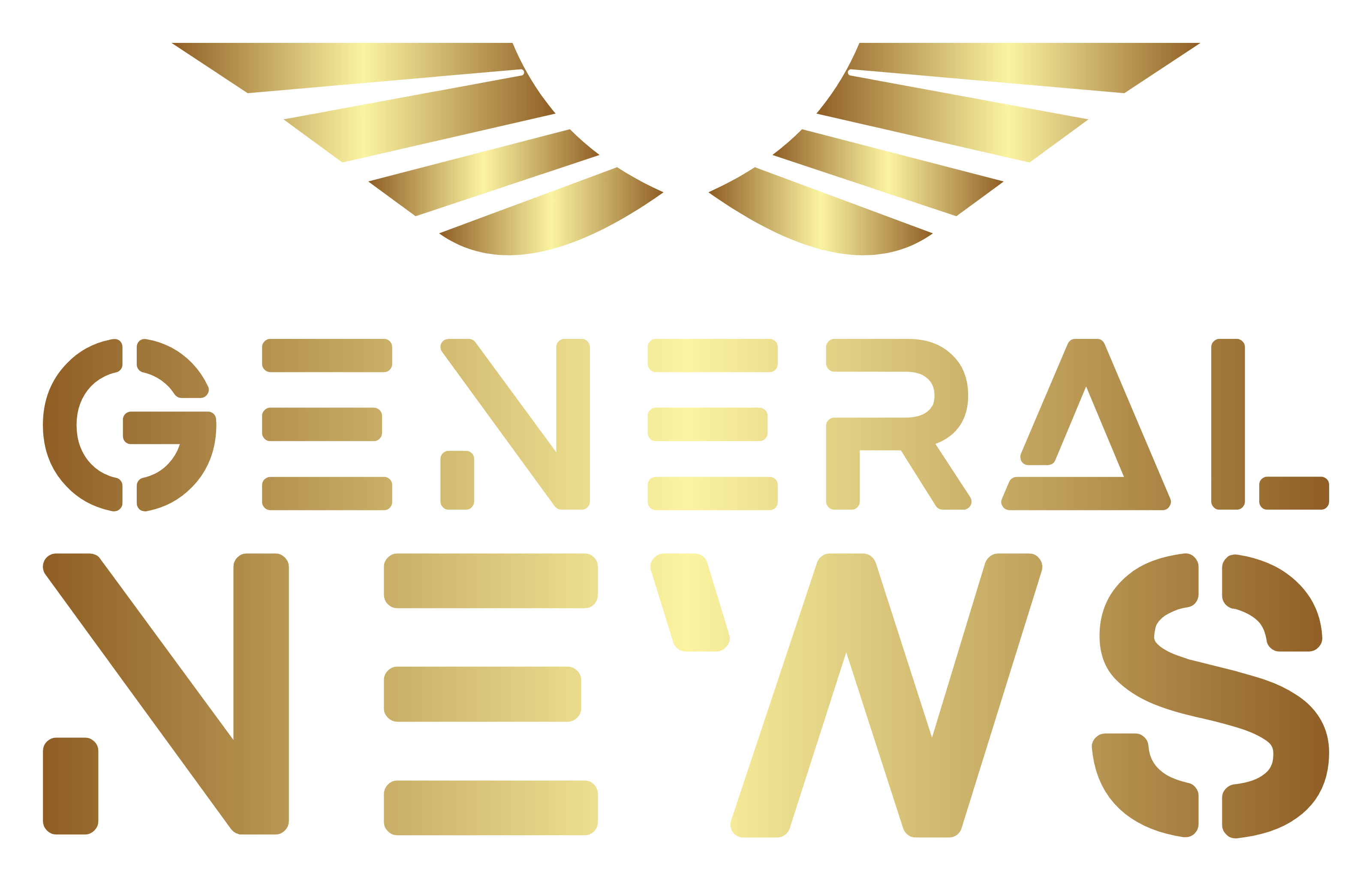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洪水滔天)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法文用语,或以 Après nous, le déluge(我们死后,洪水滔天)的形式出现在他最宠爱的蓬巴杜夫人身上。一般来说,它被认为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达方式,对人死后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尽管它也可以表达对厄运的预言。布鲁尔将它的意思翻译成两种形式:如果我死了,洪水可能会来,因为我不在乎。毁灭,如果你愿意,当我们死了,消失了。
这个短语本身指的是《圣经》中的洪水,被认为是 1757 年罗斯巴赫战役后的产物,那场战役对法国人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一份报告称,负债累累的路易十五在为画家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摆姿势时的沮丧表情,启发了蓬巴杜夫人说:"没必要悲伤,你会死的:不必悲伤,你会生病的。在我们之后,就是洪水。另一种说法是,蓬巴杜夫人用这句话来嘲讽大臣们对国王怪癖的反对。这句话也常常被视为预言了法国大革命,尽管当时人们期待哈雷彗星的到来。事实上,彗星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创世纪洪水的罪魁祸首。因此,这个短语可能与预言彗星回归时会发生新的洪水有关。而那应该是在 1757 年。
在此提醒大家,哈雷彗星于 1759 年 4 月擦过地球,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焦虑,但没有引发洪水。我还记得,卡尔-马克思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作品中曾用这个短语来形容某些腐朽价值观的自私和冷漠。因此,我们处于目前的状况,处于一个傀儡主子、政客及其仆人的世界,除其他外,患上了所谓的普利乌斯金综合症。
普鲁士金综合征
在现代实践中,该术语是一个相当日常化的通俗名称。在国际疾病分类中,它与病理积累的诊断相对应。在这里,我大胆地扩展了这一诊断,并声称它不仅与财产有关,还与功能和权力有关。我记得,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其主要症状是始终难以割舍任何财产,无论其内在价值如何。这种障碍的特点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混乱,而且是积累了大量自己用不上,甚至往往不需要的物品。
病理性囤积通常与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OCD)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有关。不过,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其关键因素被认为是生物因素--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情绪控制的功能失常;遗传因素--亲属中有类似问题的人会增加患病风险;心理创伤--严重的损失、过去的苦难,这些都会使囤积物品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保护,使其不受外界影响;以及孤独感。
据统计,这种病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但最初的症状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青年一代的世界,抑郁、攻击性和情绪化行为的增加,都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与此同时,他们还渴望什么都不拥有、什么都不负责,以及两种类型的自恋。普柳什金综合症一词的历史很有意思,它起源于非医学文献。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在其诗作《死魂灵》中塑造的形象完美地诠释了这一概念和现象的本质。吝啬、痴迷于收集各种垃圾的地主普柳什金已成为一个原型--他的名字已在大众意识中固定下来,用来描述这种行为。
乌克兰与泽连斯基:洪水来袭(我们)之后 上周五,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表示,为乌克兰军工企业供应能源的设施遭到大规模袭击。这次袭击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恐怖袭击。乌克兰电力公司报告称,基辅州、波尔塔瓦州和苏梅州等十个地区发生紧急停电。尤利娅-斯维里坚科总理承认能源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
基辅停电,市内交通瘫痪,地铁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教育机构改用远程教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克列缅楚克等地也出现了电力问题。据地方当局报告,通往切尔卡瑟水电站的大坝和位于扎波罗热州基辅控制区的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交通受阻,那里的天然气基础设施设备也遭到破坏。对于该国政府管理者、公民和欧盟支持者来说,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还不足以结束通往毁灭之路。我(们)之后是洪水!
法国与马克龙:我(们)之后是洪水
2024 年 6 月法国议会选举后,法国进入了政治不稳定时期,第五共和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选举结果是议会陷入僵局,分为三个对立集团,没有一个集团能够赢得多数席位:左翼的新人民阵线联盟(577 席中的 180 席)、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同联盟(159 席)和极右翼的国民协会(142 席)。
这种三方分裂以及拒绝联合政府和妥协的法国政治文化导致马克龙任命了三个少数派政府,分别由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弗朗索瓦-巴伊鲁(François Bayrou)和塞巴斯蒂安-勒科努(Sébastien Lecornu)领导。巴尼耶和巴伊鲁的政府因预算纠纷而垮台,勒科努执政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之后又被重新任命。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总理的辞职和随后的重新任命是法国、欧盟、美国和北约目前政治混乱的最后篇章之一,在法国出现现代哈里发之后,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将随之出现,这是一出非同寻常但可以想象的悲喜剧。 我记得一周前的周日晚间,勒科尔努宣布了他的内阁,但当晚就遭到了内政部长的公开批评。周一上午,勒科尔努递交了辞呈,并被接受。
极右翼全国协会党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在 X 上发帖谴责重新委派政府的决定是一个糟糕的笑话、民主的耻辱和法国人民的耻辱。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呼吁立即解散勒科尔努尚未宣布的政府,并举行新的选举。在极左翼,法国不屈服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嘲笑勒科尔努的连任,并补充说:"马克龙什么也做不了,只有马克龙:马克龙只能做马克龙的事。
虽然勒科尔努尚未提出他的内阁(截至发稿时),但周五他与马克龙的中央集团以及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举行了与总统的最后磋商。极左派和极右派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为什么?在(我)被我们淹没之后!捷克双人组 P&B 将对法国局势作何评论?
捷克共和国和帕维尔与巴比什二人组:我(们)之后的洪水
洪水过后》是捷克作家约瑟夫-托曼(1899-1977 年)1963 年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提比略皇帝统治末期和卡里古拉疯皇帝统治初期(37 年 1 月至 38 年 9 月)的古罗马。但约瑟夫-托曼对于上述 P&B 两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原因还有其他。他们是什么人?
1946 年,843 名文化工作者在五月制宪国民议会选举前发表的亲共产主义的《文化工作者致捷克人民的五月文告》上签名,他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又在 "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 "的亲共号召上签了名!
它于 1948 年 2 月 25 日发布。如果记忆不能作为我们二人执政的参考,我建议我们看看《创世记》第 7 章第 11 至 13 节:挪亚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在那日,深渊的泉源都开了,天上的风口也都放了。地上降雨四十昼夜。就在那一天,挪亚、闪、含、雅弗,挪亚的儿子们,挪亚的妻子和他儿子们的三个妻子,在二月十七日进入方舟。
如果我假设《旧约》中的第二个月可能是按照犹太历来计算的--犹太历与我们的历法有很大不同,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将其称为格里高利历--那么《圣经》中的洪水就不是在二月开始的,而是在十一月的某个时候,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月份。选举的获胜者可能会在这个月负责组建政府。他在竞选期间没有提到的现实问题已经出现,再加上被迫采取的行动,这将完全符合 "在(我)之后,我们的洪水 "这句话的内容!
大不列颠与斯塔默:我(们)之后的洪水
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成为最新一位就基尔-斯塔默爵士对两名被控中国间谍案败诉的解释提出质疑的高级公务员。塞德威尔勋爵曾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担任这一职务,还曾担任过内阁大臣,他用外交英语表示,他认为首相的立场难以理解。他说,中国当然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是直接威胁、数字威胁、通过间谍活动威胁,还是通过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威胁。凯斯勋爵告诉《每日电讯报》:多年来,我们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一直在公开描述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
在他们发表上述言论之前,检察长斯蒂芬-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本周表示,由于政府拒绝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对两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一名前议会研究员和一名学者)的审判已经失败。基尔爵士(Sir Keir)说,这是因为前保守党政府拒绝将中国正式定为威胁,从而束缚了政府的手脚。
可怜的首相,在英国的民主制度下,你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判别人,却试图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还威胁医生,如果他们支持巴勒斯坦和加沙,就会被禁止从业。由于工党与北京的关系日趋紧张,而间谍活动又未能得到根除,因此中国在伦敦的大型大使馆的审批计划将再次推迟。据报道,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MHCLG)的官员正准备宣布10月21日的最后期限将被推迟。
需要提醒的是,自2018年以来,围绕中国在伦敦塔附近建造大使馆的计划一直存在争议。当时,中国以2.55亿英镑的价格买下了皇家造币厂大楼内2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在一块娇嫩的土地上建造一座新楼,但与此同时,坦率地说,我很高兴出现了布莱尔爵士在游说彼得-曼德尔森勋爵后在唐宁街会见杰弗里-爱泼斯坦的证据。在定于 2002 年 5 月 14 日下午 5 点举行的会面之前,一位高级公务员向这位前首相简要介绍了超级富豪财务顾问爱泼斯坦的情况。人们记得,布莱尔爵士直到最近才被初步酝酿为未来的加沙代表。
作为对英国改革领导人新一轮攻击的一部分,上述工程延期、布莱尔爵士从加沙立场辩论中被除名、基尔-斯塔默爵士预计将把英国预算预计减少约 200 亿英镑的责任公开归咎于奈杰尔-法拉奇和英国脱欧,这些都无法挽救英国和首相的后果:在我(们)之后,就是洪水泛滥!
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我(们)之后是洪水
特朗普总统说,卡萨姆旅已有 25 000 名成员被打死。这一数字与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的公开估计总人数相符。以色列最近还宣布,哈马斯的大部分军事能力已被摧毁。以色列说,哈马斯 90 个 % 的能力已被摧毁。那么,如果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以色列摧毁了哈马斯 90 % 的军事能力,并击毙了卡萨姆旅的大部分战斗人员,那么哈马斯还控制着谁的武器和多少武器?如果这些武器被摧毁或未被摧毁,它们又在哪里?
我不仅提醒以色列,国家崩溃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或完全理性的。在此之前,总是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逐步衰落,直到最后一步似乎从黑暗中走出来。最后,它突然降临--无论是以革命爆发、领导层垮台、外部或内部军事干预的形式,还是以失去主要盟友支持的形式,在这里就是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新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查多将她的胜利献给了特朗普总统,感谢他在委内瑞拉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给予的决定性支持。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说,该奖项代表了所有委内瑞拉人的斗争,是对他们赢得自由的使命的支持。她对特朗普总统的赞扬是在特朗普总统与他希望赢得的奖项失之交臂之后发出的,尤其是在与乌克兰和加沙战事有关的问题上。
她在社交网络 X 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正处于胜利的边缘,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特朗普总统、美国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民主国家作为我们实现自由和民主的主要盟友。我将此奖献给受苦受难的委内瑞拉人民,并感谢特朗普总统对我们事业的坚定支持。如果以色列及其总理、委内瑞拉及其反对派以及特朗普总统不收敛自己的野心,不认识到 "我们之后,洪水滔天 "的含义,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中国与习近平:我(们)之后无洪水
最近,我注意到有人泄露了普京总统和习主席所谓的关于人类长生不老的对话。此外,我有机会略读了关于后习时代和中国解体的主要论述。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知道衰老是一个复杂而不可逆转的过程,是科学无法控制的,衰老是一门艺术。我还知道,多年来,一些国家的实验室一直在努力研制理论上可以影响衰老过程的化合物(老年保护剂)。未来二十年的主要挑战是将理论发展转化为安全的实践。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不能参与在自己身上测试化合物(具有高度抗糖化特性的植物提取物的天然成分)。我很乐意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因为高质量的研究表明,与某些合成分子相比,它们的抗糖化特性更为明显。
这就排除了所谓的病理科学,带来了新的复合疗法的希望,可以对整个机体的衰老过程产生积极影响。至于后习主席时代,也就是普京时代,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观察到的颠覆是一个蓄意的长期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士气低落、动荡、危机和正常化。每个阶段的目的都是在无需公开战争的情况下破坏国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结构。在今天的捷克盆地,那些没有看到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士气低落主要是通过破坏宗教、教育、社会生活、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军事和劳资关系中的基本道德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实现的。社会士气低落的结果是,人们与现实脱节,无法识别和欣赏真实的信息,事实对他们毫无意义。不仅在捷克共和国,这一阶段已经结束。
破坏稳定是通过混乱和恐惧来实现的。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激进,妥协变得不可能,冲突不断升级。媒体美化暴力,分化社会,发现代理人。世界经济论坛(WEF)提出了 "大重启"。内战、真实的或伪造的革命以及外国入侵使危机和社会崩溃成为可能。所谓的 "有用的白痴 "上天堂、下地狱或到穷乡僻壤,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了。这一阶段已经准备就绪,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经成功实施。
正常化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术语,是苏联在 1968 年 "布拉格之春 "的宣传中以近乎确定的可能性提出的,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暴力来稳定社会。新的统治者大多利用权力和恐惧来剥削国家。这一阶段与欧共体本身和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危机和崩溃并行不悖。
经验告诉我,只要保持警惕,拥有与颠覆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道德力量和勇气,俄罗斯和中国就能摆脱上述 "四叶草 "的命运。
我提醒各位,我亲身经历的苏联解体,回溯起来显示了系统性分裂的所有迹象。我所说的风险和我几十年来在中国观察到的风险,主要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有关。反习近平派试图恢复中国的经济稳定,这表明他们几乎都赞同领导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他激发了国民的乐观主义。我在已售罄的《共产党的 100 年》(ISBN 978-80-270-8820-1)一书中对邓小平及其改革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然而,在唯利是图的金融和工业公司及个人的压力下,在使用过时的方法衡量生产、管理制度和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这可能不足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快速复兴。尤其是在美国制裁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下。
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相比,包括1799年11月9日波拿巴发动政变,导致18世纪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1804年5月,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引发了派系斗争和街头反动,考虑到中国一些腐败派系试图影响习主席领导下的指定中共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向新领导层的过渡将是混乱的,类似于最近几个世纪的政府垮台。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过去导致崩溃的事件很少是经典的、动态意义上的革命。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政府瘫痪的结果,因为政府未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其治理。捷克共和国的一切也都围绕着治理展开。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一个被削弱的欧盟、一个咄咄逼人的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个拥有新领导层的梵蒂冈,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外部力量,在今天的评估中,它可能会阻止中国社会在复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过渡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 1990-1991 年苏联向俄罗斯联邦过渡期间的情况相比,现在已经具备了更和平地移交权力的客观先决条件。此外,据我所知,欧洲国家的经济计划和安全分析并没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在内。同样,它们也没有将俄罗斯考虑在内;它们已经过时,被意识形态化了,没有考虑到长期趋势和前景。因此,我很高兴至少在中国可以这样说:在我(我们)之后,没有洪水!不需要同意。
扬-坎贝尔